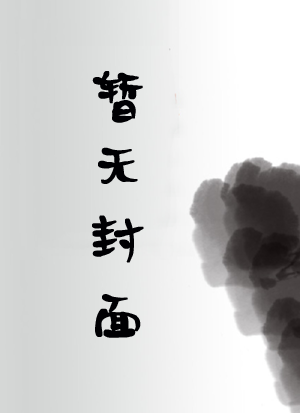終究還是忍耐住了。
男人輕輕地撫摸着她背後,像哄小孩兒,聲音被她堵了一半――
“餓了麼?不着急,一會我給你打飯,你嗓子疼,要吃清淡的稀粥。”
他一向不是話多的人,此刻溫言細語,格外溫和,任由她胡亂親着他薄唇放肆。
可甯媛沒松手,但松了嘴,擡起大大的眼,定定地盯着他:“你......洗澡......”
她聞見他身上很幹淨清新的肥皂味。
榮昭南不知道她為什麼問自己這個問題,點頭:“下午折騰設備出了汗,來之前洗了澡。”
她看着他身上硬朗的沙漠迷彩,又指了指外頭:“還要......”
“嗯,八點半要試驗比較其他裝備,這套迷彩是E國的沙地新裝,也有配套設備。”榮昭南低聲道。
他們現在弄到這些國外的東西格外不容易,想要知道自己與世界的差距,必須要抓緊時間記錄下裝備的體驗感。
甯媛好像松了口氣,努力用氣聲說:“最少......一個半小時。”
榮昭南以為她說空出來一個半小時可以吃飯,他點頭:“嗯,我有一個半小時能陪你吃飯。”
可甯媛左手沒松開他的領子,卻用那隻掌心包紮着紗布的右手,向下摸在他腰間的武裝帶上。
他身上的英制沙漠迷彩灰白暗黃交織成掩護色,領口扣得很緊,把喉結都護住。
冷色調的迷彩服是讓人聯想起鋼鐵、血與沙漠烈陽下的硝煙。
他腰間粗粗的編制武裝帶黃銅鐵扣上印着英文字母,粗犷冷酷,卻把他修腰勒得緊窄。
顯出一種勾人的禁欲範兒,還有那張高冷俊美又鋒利的臉,此刻卻溫情地看她。
像鋒利的刀刃入了刀鞘,想讓人把他拔出來!
“不吃飯......吃......你。”她張嘴,艱難地吐出幾個字。
榮昭南頓住了,看着跪在床上,趴在自己懷裡的姑娘。
這才發現,她眼裡的光,不太正常。
有點像和匪徒搏鬥那天晚上,明亮到一股子兇狠氣。
榮昭南眉心擰了擰,按住她放肆的手:“你身上還有傷,我沒那麼禽獸。”
甯媛眼睛亮得吓人,像跳着那天晚上的火焰:“傷......在脖子,在手......不影響......”
她不放棄地去解他的武裝帶,無聲地開口用氣音告訴他,她想要什麼。
榮昭南眼底閃過暗流,卷毛兔是真的不太正常,怕是創傷應激了――
這是越戰後A國發現士兵一種精神受刺激的後遺症。
他眉心擰得更緊,卻不敢太用力地去拉她受傷的右手,隻能喑啞地低聲道:“甯媛......唔!”
甯媛那隻完好的左手突然那探入他迷彩服下擺,毫不留情地隔着褲子。
一把準确握住了那把專屬于他的軍刀,往外抽。
就像那天她握住那把砍死了高大匪徒的長砍刀一樣,用力拿捏住專屬于他,沉甸甸的危險的軍刀。
榮昭南渾身猛地一僵,阻止的話變成了悶哼,向她的方向斜了身體。
她頭上脖子上包着紗布,笑起來時烏黑明亮的大眼彎彎,看起來純真得像個未成年少女――
“好刀,就是不知道這刀快不快,能砍死我麼?”
撩得榮昭南眼底閃過一絲狠戾的焰火兇光,但片刻後,又生生壓回清冷幽暗的眼底。
他一把清冷的聲音都壓抑得溫和,輕輕拍她尾椎:“别鬧,放手,你病了。”
甯媛卻湊在他敏感的耳邊,用氣聲在他耳邊親昵又老氣橫秋地笑――
“榮隊,教材都看完那麼久,床上打仗還是不行?”
他是細緻的人,但他的細緻都用在對付敵人上,從不是真禮貌斯文的人物。
太歲這張淡漠漂亮面皮下是一頭野獸,一把淬煉見過血的刀。
現在,她要他這把太歲刀,捅穿附着在她靈魂身體深處的焦躁和不安。
榮昭南頓住了,低頭看她,慢慢地笑了:“你會後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