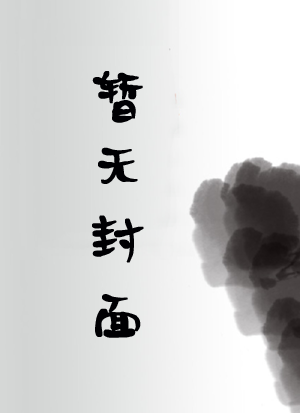第一卷 第772章 宗主也被定住
沒有人能想到,天道宗那位傳說中的大乘期巨擘,那位威震整個地心世界的宗主,竟然會是這樣一位看上去隻有二十多歲的絕色女子。
大乘期修士,壽元綿長,可達萬載,即便容顔駐世,也極少有人能将容貌維持在二十多歲的模樣,這般年輕,這般美豔,又擁有這般恐怖的實力,簡直就是世間奇迹。
實際上,這位女子,便是天道宗宗主,龍青甯——一位活了近千載,卻依舊容顔絕世,修為高深莫測的大乘期巨擘,乃是整個地心世界,最頂尖的強者之一,一手建立天道宗,憑一己之力,将天道宗發展成地心世界數一數二的修真門派,威懾四方,無人敢惹。
龍青甯緩緩走到山門之内,目光冰冷地掃過僵在原地的七位長老、兩位弟子,又緩緩落在張成身上,眼底的殺意,愈發濃郁,周身的威壓,也愈發磅礴,仿佛要将張成瞬間吞噬。
她正要施展大乘期的神通,将這個膽大包天、闖她山門、困她長老的狂徒,挫骨揚灰,永世不得超生。
張成神色淡然,臉上沒有絲毫畏懼,甚至連眼底的波瀾,都未曾有過一絲。
他輕輕擡起右手,再次打了一個清脆的響指,語氣平淡,卻帶着一股掌控一切的力量,依舊是那個簡單的字:“定。”
下一秒,詭異的一幕,再次發生在所有人的眼前。
那位威震整個地心世界的大乘期巨擘,天道宗宗主龍青甯,瞬間僵在了原地,身形一動不動,周身那磅礴的威壓,瞬間停滞,那濃郁的殺氣,也瞬間凝固,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一般。
她臉上的冰冷與殺意,徹底凝固,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,依舊清澈透亮,卻失去了所有的神采,變得空洞無神,連一絲一毫的動彈,都做不到,如同一個精緻絕倫的雕塑,美得驚心動魄,卻又詭異至極。
大乘期巨擘,竟然也被定住了!
張成緩緩來到淩清瑤的面前,目光緊緊盯着她那張嬌豔絕倫的臉蛋,眼底閃過一絲驚豔與好奇,輕輕捏住了她的臉頰,觸感溫潤細膩,如同上好的羊脂玉一般。
“哇塞,這麼漂亮?皮膚這麼好,滑溜溜的,你到底多少歲了?看上去才二十出頭,竟然就已經是大乘期了?也太厲害了吧!”
他語氣中滿是驚訝與好奇,聲音不大,卻清晰地傳入了在場每個人的耳中,打破了山門的死寂。
宋馨和卡佳,徹底驚呆了,臉上的崇拜,瞬間被極緻的震驚取代,雙眼瞪得圓圓的,目光死死地盯着張成,又看了看被捏住臉頰、僵在原地的龍青甯,腦海中一片空白,隻剩下張成那句話在耳邊不斷回響。
她們萬萬沒有想到,張成竟然如此強大,能定住大乘期的修士,而且敢如此放肆,竟然敢捏她的臉蛋,還敢如此随意地詢問她的年歲,這簡直就是無法無天,是她們從未想象過的事情!
天道宗的所有人,無論是僵在原地的長老、弟子,還是聞訊趕來、躲在一旁圍觀的内門弟子、雜役弟子,皆徹底傻眼了,眼底滿是驚恐與難以置信,臉上寫滿了絕望。
他們的宗主,那位威震四方的大乘期巨擘,竟然被人輕易定住了,還被人捏住了臉頰,如此羞辱,這簡直就是天道宗千百年以來,最大的恥辱!
那位傳說中,擡手便能毀天滅地,距離飛升成仙僅有一步之遙的大乘期巨擘,在這個年輕男子面前,竟然如此不堪一擊,連反抗的餘地都沒有,這簡直就是颠覆了他們所有人的認知!
前來拜師的家長、孩童,更是吓得魂不附體,癱軟在地,雙目呆滞,連哭都忘記了。
他們今天,竟然親眼見證了一場神迹,一個金丹大圓滿的修士,輕易定住了七位高階長老,還定住了一位大乘期巨擘,甚至還敢羞辱大乘期巨擘,這等場景,怕是他們這輩子,都不會再見到第二次!
整個天道宗山門,徹底陷入了死寂,隻剩下風吹過林間的輕微聲響,還有所有人沉重而急促的呼吸聲。
所有人的目光,都彙聚在張成的身上,眼底滿是難以置信的震撼與敬畏,他們心中都清楚,從這一刻起,天道宗的威嚴,徹底被打破,而這個年輕男子的名字,注定會傳遍整個地心世界,成為一個傳奇,一個無人敢惹的神話。
“我是用時間法則禁锢住你的,等下我給你解開,你最好别動手了,否則,我直接把你禁锢抓回去做老婆。”
張成的手指依舊輕捏着龍青甯溫潤如玉的臉頰,指腹摩挲間,能清晰感受到那吹彈可破的細膩肌理,眼底的驚豔未減,語氣卻添了幾分戲谑的調侃,似真似假地吓唬着眼前這尊動彈不得的大乘巨擘。
龍青甯那凝固的眉眼間,似有不易察覺的蹙動——她雖被時間法則定在原地,無法言語,無法動彈,連呼吸都還停留在方才盛怒的瞬間,可神魂深處的羞辱與憤怒,卻如燎原之火般瘋狂蔓延,幾乎要将她的理智焚燒殆盡。
她乃是天道宗宗主,活了近千載的大乘期巨擘,隻差一步便能掙脫凡塵桎梏,飛升成仙,縱橫地心世界無人能及,何等尊貴,何等威嚴?
可如今,卻被一個看似金丹大圓滿的修士輕易禁锢,像個玩偶一般被人捏住臉頰,甚至被如此輕佻地戲言,這份恥辱,比殺了她還要讓她難以承受。
金丹修士?
一個區區金丹修士,竟能淩駕于她這大乘巨擘之上?
這簡直是天方夜譚,是她修行千年以來,最丢臉、最荒唐的一刻。
張成瞧着她眼底雖空洞卻難掩的戾氣,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,手指緩緩收回,時間異能也收回。悄然斂去。
下一秒,所有被禁锢的人皆恢複了自由。
兩位守門弟子踉跄着後退兩步,手腕依舊微微發僵,看向張成的目光裡,早已沒了先前的鄙夷與憤怒,隻剩下深入骨髓的恐懼,連擡頭與他對視的勇氣都沒有;